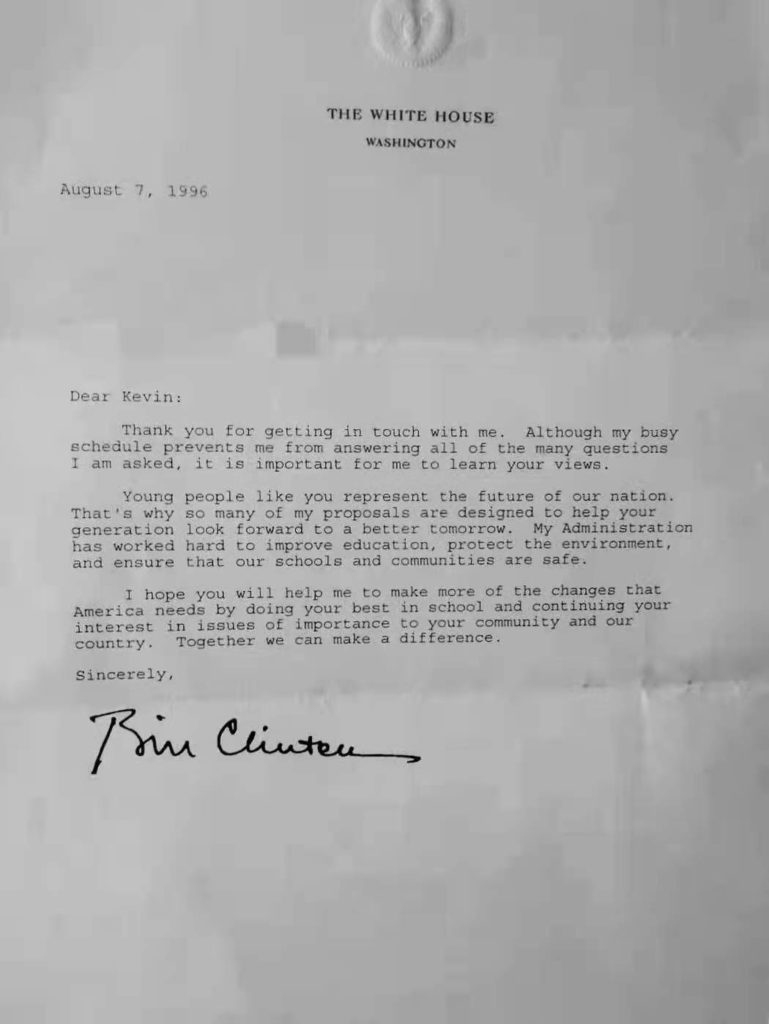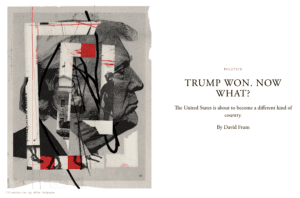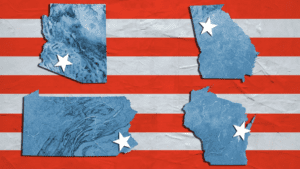作者:孔捷生
俄乌战争未打响之前,克里姆林宫的“御桌”先火遍全球。那就是普京御用长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匈牙利总理奥班,坐在御桌远端,远到肉眼看不清对方表情。这是外交会晤还是藩邦朝觐?
还好,这些藩王尚可坐在长桌另一头,而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古面圣,则尊卑有序,下属只能委曲卑微地坐在远端之侧,就像礼部尚书、兵部尚书不配和皇帝对面平坐。
再看泽连斯基,与子同袍,与民同仇,与危城共存。还有英国金毛首相鲍里斯在基辅街头和市民交谈、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到布查实地察看……却要问,开战以来普京在哪里?除了在御桌遥远的一端,没再见过他。
这说到一个烧脑话题,何为最远距离?地理学家答:北极到南极的距离;天文学家答:不同星系的距离以光年计算;诗人答:是夏天与冬天永不相见;有一位已失和的朋友说:人际之间最远的距离是三观不合。而我觉得,无论是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很难用抽象答案去度量。还是说点个人经历吧。
我近不惑之年始来美,接受角色转换甚难。不同于九岁的儿子,他像幼苗舒展,自由生长。我却像一片飘零之絮,委落泥尘后艰难重生,我将摸索认知异国文化视为精神逆成长。
成长就像打开一重重人生之门,步入另一境界。我儿子在新泽西读中学,十五岁时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质疑公校教育若干问题。殊不想收到白宫信函,竟是总统回信并附送一张签名照片。
克林顿首先感谢我儿子来信,说:尽管他公务缠身,但你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你代表着美国未来,我们将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关乎下一代的问题……等等。这些话很笼统,但措辞平等亲切。
儿子很高兴,带回学校给同学传阅。作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我们也觉意外,并为儿子的欣悦而欣悦。
然而,成人认知毕竟异于成长期的孩子。我们很快了解到,投书白宫,除却无厘头内容,都会得到回复。白宫有专门公关班子,以总统名义给民众回信是其职责之一,连信末和照片上的总统签名,也是逼真影印。但做父母的并未跟儿子揭破,让他自己从生活领悟,才是成长扎实的脚印。何况,日后他对美国社会之融合,要比上一代深入得多。
我的成长期曾有一段红色记忆。周总理爱民如子,只要见一面握过手,哪怕多年之后重遇,也能记住人家的名字。这个传说在知识分子中流传最广。后始知美国也有神人,克林顿总统亦具“人面识别”超人本领。二度见面被他亲切唤出名字的人,无不感动——如果这词太煽情,至少是触动吧。
只不过,美国并无铸锻领袖神话的习惯。我其后得知,克林顿在白宫与来访者见面,出场之前,幕僚会指点视像或图片,告诉总统该人名字与背景。说来并非所有总统都练这门功课,克林顿却做到了。
希拉里则是另一型格,她的明灿笑容抹不去精英的高冷。倘非如此,2016川普能否入主白宫尚未可知。记得当时希拉里无甚兴趣去锈带拉票,称潦倒落魄的白人蓝领“可悲”。我曾经驾车经过破败锈带,直觉上那是弃地与遗民。我也想说“可悲”这个词,她却万万不能说;我不是解决问题的人,她应该是。显然,她不是。
希拉里失去锈带民心后才痛心疾首:“美国分裂的程度,超过我们的想像。”我在想,如果是克林顿,他当时会怎么做?
我后来迁居大华府,听到不少逸闻。哪怕不喜欢克林顿的政界商界人士,多认同他确有个人魅力,只要现身公共场合,俨然聚光灯追身,他自己就是光源。我有亲身经历可佐证——
90年代中一个圣诞节,我陪来美探亲的父母到华盛顿观光。别的城市每逢节日都熙熙攘攘,惟此城例外,只缘首都上班族逾六成都不在市区居住。
我和两老闲逛,只闻圣诞音乐在空旷街道飘荡,温馨而寂寞。我们行至一向游客如织的白宫,居然也清冷得可以。白宫南草坪只有一条人影在遛狗,我没去留意,只觉得正是照相时机,免得摩肩接踵。
留影毕,此际草坪遛狗者扔出的网球滚到栅栏边,那人过来了,他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这才认出来正是克林顿。
那时距911还有几年,完全看不到特勤保镖踪影。白宫栅栏外就是街道,克林顿离我们仅六七步。他生就一副阳光脸孔,笑起来显得很真诚的样子。这正是他自带流量的天赋。
我后来推断,他逗狗的网球是有意掷到栅栏边的,休闲时刻不忘亲民秀,能把这视为己任并享受其中,我想首推克林顿。
至于小布什,虽远不如克林顿,胜在性格憨直;奥巴马也很注意亲民,但有时表演着了痕迹。说到川普,他的本事是激发基本盘死忠追随之余,却唤起更多反对者。
无论哪一任总统,都不值得赞美讴歌。美国绝少听到颂圣谀词,即令克林顿在任时亲和力爆表,也一样被民众怒喷。我亲历的另一故事,克林顿总统正是其中角色。
1999年女足世界杯中美对决,是足坛盛事。美国男足乏人关注,却是世界上踢球女性最多的国家,足球力压垒球篮球,是热度第一的女子运动项目,每逢大赛事,上座率远胜男足。我想这和中小学女足普及和无数家长的忘情投入有关。
那届世界杯,中美女足过关斩将都如摧枯拉朽。决赛两强对撼,全美热爆。我躬逢其盛,飞到洛杉矶看球。
当日赶到玫瑰杯体育场,恰巧克林顿总统夫妇也在此刻到达。或许他们当时读高中的千金也踢球,更大可能是惯做亲民秀的克林顿不放过蹭热度之机。总之我和美国总统再度相遇。
这次克林顿夫妇并不讨喜。为让总统一行进场入座,特勤保镖暂时封锁通道。我的球票正是这个看台。虽只迟滞片刻,被拦截的老美们却不干,齐齐报以嘘声,唾沫星儿快喷上希拉里的秀发了。克林顿夫妇只得陪着笑脸快步通过,及至保镖们魁梧的背影消失,大家随后鱼贯而入。
我的球票座席就在总统邻区,要经过已落座的克林顿夫妇面前。一黑一白两名特勤人员陪着小心,温言引导人流尽快通过这条过道。这“黑白双煞”西装革履,举止已十足斯文,但入场球迷心里已经不爽,对总统保镖便无好脸色。
我前面抱着婴儿的白人男子怒骂:“Fxxx!你没看见我抱着小孩?”其尖厉音频足以让美国总统听见。但无论是克林顿夫妇还是特勤组都得保持风度,听到民众以F开头的词句,也要装孙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民众的孙子,而不是大爷。
亲眼目睹美国人当面臭嘘和“F”国家领导人,这于来自另一文化背景的我可谓一种启蒙。
无论哪届总统,权力认受性都来自选票。他们亲民是必须的,只有做得好与差之区别。然而,另一体制的权力者则不同,他们是人民领袖,是用来爱戴的。
再说一件亲历之事——1987年我到首都机场搭乘民航飞机,那时未有居民身份证,个人证件都是工作证。当然有的人或有不止一种证件,比如我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省政协委员证。购买机票时个人证件不管用,必须有单位证明。
几十年一贯制的社会格局及其价值标准,个人什么都不是,能证明你是谁的只能是单位。单位俨然全能社会的微缩。
我家在北京,工作单位却在广州,每次从京南返,都要找中国作家协会盖章出具证明。与之匹配,购买机票就用中国作协会员证,但那次在首都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一时找不到,只好拿出省政协委员证。那本红封皮上印着金色国徽的证件,与中国作协的盖章证明对不上号。然而在官本位社会,那不算个事。政协委员不是官,却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登机之后,才发现官本位“福利”不止于此。明明是普通经济舱机票,我却被安排坐头等舱。那是我头一回享受这等待遇,便事事新鲜,却发现前三排一直空着。及至起飞前一刻,始见一帮人登机,被簇拥入座的原来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姓李,单名。
副总理出行并无专机,与民同行本是好事,可零距离了解民情,更是做亲民秀良机。
那时我对西方政治家素质无甚认知。但就官本位社会而论,就我所见,这位副总理也算是对民众最冷漠的一个。他坐第一排靠窗位置,身边与后排都是随员与便衣警卫。连笑容可掬的空姐送饮料,都是随员代接转递,他头也不抬,连道谢都有人代劳。京广航线就两个小时多一点,全程不见他离座与其他旅客和空服人员交谈。
倒有花絮,我在候机厅偶识一位香港旅客,他是北京首家中港合资酒家(在前门东大街)点心师。因粤语同声同气,大家聊得来,但登机后就隔开了,半途他要到头等舱来索要联系电话,却被便衣警卫拦住,不得越界。
我这才明白,坐头等舱并非政协委员证带来的福利,而是登记时“政审”的刻意安排——政协委员身份给大领导带来更多安全感。
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全机旅客都端坐不动,让国家领导一行人先下机。革命经典黑白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有句台词“让列宁同志先走”;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孩子们化为灰烬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是“让领导同志先走”。这守则来自体制深层结构。
当副总理经过我身边,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符号,那是严肃、矜持、倨傲的混合。不由不信,如果某人天生就没有亲切感,那么后天也学不来。人与人心理距离之遥远,从价值体系就是先天的。
及至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更多表情包,把他固化为脸谱人物,更把他与某个历史事件永远捆绑。
我到了异国,一切都从头去学。儿子轻而易举完成的文化转换,我却要花几倍时间。终于迈过那道门槛,便洞悉西方政治家都“装”,装着装着,就成了价值标准与行为守则,这可是弄假成真了。
驀然回首,发觉当日邂逅之大人物,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就是不装,完美做到了他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