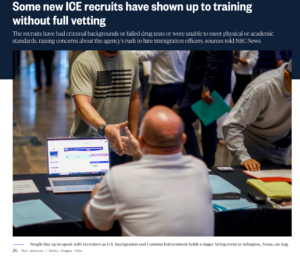本文系作者原创,授权“美国华人杂谈”独家发布。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发。
时值抗战胜利80周年,写点纯属个人的感受。我曾提到族中亲戚有两位飞虎队成员,只缘我母系血脉来自广东侨乡台山,早期来美的已开枝散叶。二战中参军的华人有1.3万至2万,是参军比例最高的族裔之一,投军者占当时华裔总人口的17-22%。
我的家族中有一位华二代参军成为飞虎队昆明机场的地勤。另一位并非在美华人,他在飞虎队协助训练国军飞行员时被认定为可造之才,便送到美国深造,完成特训后回国抗敌。及至1949年,他赴台而后辗转来美。
36年前我初履美国,这两位亲戚都很有亲情,给过我不少帮助。如今他们都过世了,惭愧的是,我对这两位亲戚的抗战故事所知甚少。
家族中有多位血缘更近的亲人是抗日老兵,国共两边都有,当时他们与整个国族一样,都投入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浩大战争,他们的命运和国家存亡嵌合,宛如长城灰扑扑的墙砖。
外婆家的青花瓷罐
我从未见过外公,他留给我的全部印象只是一个石胎青花瓷骨灰罐,在外婆家厅堂供奉。记得一年中只在忌日、清明和大年初一这些日子,那尊静穆的青花瓷罐才被唤醒。它隔着袅袅香烟端详外婆、子女和他生前无缘得见的一群孙辈。到我稍长大些,才知外公是抗战烈士,却是另一边的,所以母亲甚少向我提起外公往事。
才读初一的我注定要在动乱中蜕去少年的蝉翼,时代狂飙夷平了无数事物,外婆家的祭祀也停了。关于外公,长辈们益发沉默,在那个风雷怒响的苦夏,外婆家的青花瓷罐忽然消失。我母亲不敢多问,只能猜度罐中骨灰已随疾风飘逝。
我15岁离家远行当知青,就算听过家史一鳞半爪,但人都未长成就踉跄走进陌生天地,家族记忆太遥远了,15岁的人生没有往事,只有眼前一片茫然。及至从琼崖返城,我廿岁出头,青春碎片却已掩埋于五指山热带雨林,从手到心都结出硬茧。不久天下斗转星移,外祖父的身世轶事不再是禁忌。此时我才知道外祖父是国军上校,在柳州殉国。
其后我成了作家,却觉得自己所见所思都写不完,无暇追寻外祖父弥漫着战火烟尘的故事。直到我的命运之舟漂移到美国,渐地觉得以前熟悉的变得遥远,原来觉得遥远的却被拉近。十年前,我用现代通信工具对身历抗战的家族中人逐一做了访谈,当时是为了留下家族记忆,没想到十年后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
外公叶博融,字君略,1900年生人,燕京大学毕业,抗战前在广州市政府工作。广州沦陷,他作为公职人员没和家人一起逃难,而是投笔从戎到珠海打游击,彷佛遁入珠江三角洲的青纱帐,茂密蔗林在湿润南风中挥舞着锋利蔗叶,如同寒芒闪烁的刀丛,隔断了他的音讯。及至外公重新露面,已是四战区政治部上校军官。
四战区司令部在柳州,此处地质构造与桂林相同,多奇山奇石。司令部所在的窑埠镇背依蟠龙山,1941年6月,蟠龙山溶洞军火库猝发大爆炸,此刻疏于职守的库长不在其位。外公从司令部赶到现场,但见人仰马翻,弹片横飞。冒死不退的外祖父指挥军民疏散,直至一波地动山摇的爆炸导致山体滑坡,外祖父颅骨被飞迸岩石击穿,脑浆溢出。
事发后幸存者都记得外祖父屹立于硝烟中的身影,说若非这位军官临危不惧指挥疏散,死难人数将不堪设想。
杨姓库长是何应钦亲戚,事发后被逮捕,何应钦索要此人交由重庆军法审判,被四战区司令部拒绝,张发奎将军下令枪决库长。四战区为十二名死难官兵建立烈士陵园,纪念碑由张发奎题词。外公军阶最高,群茔中墓碑最大。
人类各部都笃信陵墓与碑铭比人和时代更长久,这个定律很靠不住。坟草黄了会再青,石头却不然。其后纪元更迭来得匆忙而且激烈,没等青苔填满碑铭刻凿的凹痕,那些名字就湮没了,连那座陵墓也一并消失在浓稠尘埃之中。

我少年时熟记的宏大叙事,唯一主角是没有面孔的人民。后经动荡青春的磨洗历练方悟出,只有个人叙事和家族记忆才是历史的真实拼图。这一顿悟使我成为作家。
回眸我的成长期被塞了一脑子滥情话语,所有英雄都被演义化。那时以为只有疆场上马革裹尸、刑场上慷慨赴死才堪称烈士。随着阅世愈深,始知保家卫国的终极意义,不在井邑山河,而在于人的生命。外公仅用41年就走完他的一生,逃难返回台山乡下的外婆接到四战区司令部用铁皮公文箱寄来的遗物,里面仅有换洗衣服和书刊,竟无分文。
美国参加过二战的一辈人被称为“伟大的一代”。这个称谓源自记者汤姆·布罗考的纪实畅销书《The Greatest Generation》。这代人为道义而战,为远方从未见过的人们而战。那时的美国堪称真正伟大。
中国也有这么一代人,他们为国家民族和骨肉亲人而奋起抗战。我读作家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便联想起我的先辈,他们也是伟大的一代。
更多亲人的抗战记忆
家族在柳州留下的雪泥鸿爪,还不止外公的忠烈故事。1943年,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一群烈士遗孤从韶关接到柳州,我母亲被分配到柳州中正小学教书,在四战区花名册增添我母亲为准尉附员,可领取微薄津贴,除了吃饭只够买一块肥皂洗衣服,还有每月和几个老师去吃一碗红豆沙糖水,此为母亲少女时代仅有的甘甜。
我的另一血脉源头也蜿蜒到了柳州——我父亲是流亡学生,加入抗日演剧七队到四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水车》《塞上风云》《秋后》等剧目,以及《救亡进行曲》《抗敌歌》《大刀进行曲》《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歌咏节目,也曾在国共游击队掩护下潜入敌占区宣传抗日。一次演剧队到桂林,我父亲顺道到柳州会同学,此行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时柳州窑埠实验小学郑黎亚校长是中共地下特别支部成员(后任第四任特支书记),因缺师资,校方不希望国民党县政府派人进来,郑黎亚校长便向演剧七队吴荻舟(中共地下党)队长要人,让我父亲留下任教。父亲母亲此前是韶关四战区子弟学校志锐中学的同学,两人于柳州重逢,还须经过更多烽火磨难才得以结合。
柳州窑埠实验小学是直属军部的学校,张发奎无子嗣,他的养女养子及参谋长吴石、副参谋长陈宝仓的女儿都在这间小学就读。张发奎是中国现代史的另类人物,另外两人均为中共秘密党员。1950年,吴石中将、陈宝仓中将被叛徒出卖,在台湾被军事法庭处决。
同为烈士遗孤的二姨却在家族故事的另一章,她在临时省会韶关读初中,参加了高年级同学组织的读书会,憧憬“山那边哟好地方”。而后二姨纵身跃入另一条命运川河,15岁就参加了东江纵队,成为抗日女战士。
四战区司令部另有一特殊人物,是长官部少校孙慎,我外公是政治部上校,两人是同事却身份迥异。孙慎是中共地下特别支部第三任书记,他是海峡两岸传唱至今的《救亡进行曲》的作曲者,他还写过《生命诚可贵》、《前进》、《游击歌》、《慕寒衣》、《大家看》、《春耕歌》、《我们是民族小英豪》等抗战歌曲。是他发展麦新(《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作者)为秘密党员。

很多年后,孙慎成了我岳父。他享年105岁,于2021年去世,化为聂耳、冼星海那一辈音乐人最后消逝的背影。
1944年深秋,日寇发动一号作战,桂林柳州相继失守,我母亲和其他老师带领全校小学生逃难,历尽艰辛逃到贵州独山,日寇掩杀而至,只得分散突围。盟军飞机撒下传单,指示难民要走小路,盟军战机将封锁公路。
我母亲奉命丢弃行囊,带着这群小学生穿越崇山峻岭继续逃亡,宛如电影《黄石的孩子》的情节。
途中母亲和这群小学生与其他逃难师生失散,此刻惟有十八岁的母亲是这群苦海孤雏最后的依靠,她领着孩子徒步穿越崇山峻岭逃向惠水,只记得黑黝黝的峭壁挤压盘陀小径,交织着硝烟的惨淡日色勾勒出峰峦林际的轮廓,却无法投射进隘谷鸟道,但闻啼猿与鸟雀惊起的扑簌声,夹杂着野兽凄厉吼叫。
母亲一路扶持,将孩子们从死神之翼下带出来。母亲超乎年龄的坚毅勇敢一踏入惠水县城就倏然崩溃了,她领着孩子们找寻其他师生,泪水却如决堤般奔涌……98岁的母亲说起这段往事,依然老泪纵横。
我在整理口述史时,我发现家族中几辈人身处大时代,在生死间不容发之际都有一种近似的姿态,如同微末萤火飞向无边黑夜,哪怕寒露打湿牠的薄翅,吞噬牠的微光,却留下飞翔之姿,挣扎着擦出生命的亮度。
于是念及我自己的人生历程亦充满跌宕,我相信那是一种道统传承,好比外婆家的青花瓷罐,其实并没有在历史尘烟中消失。